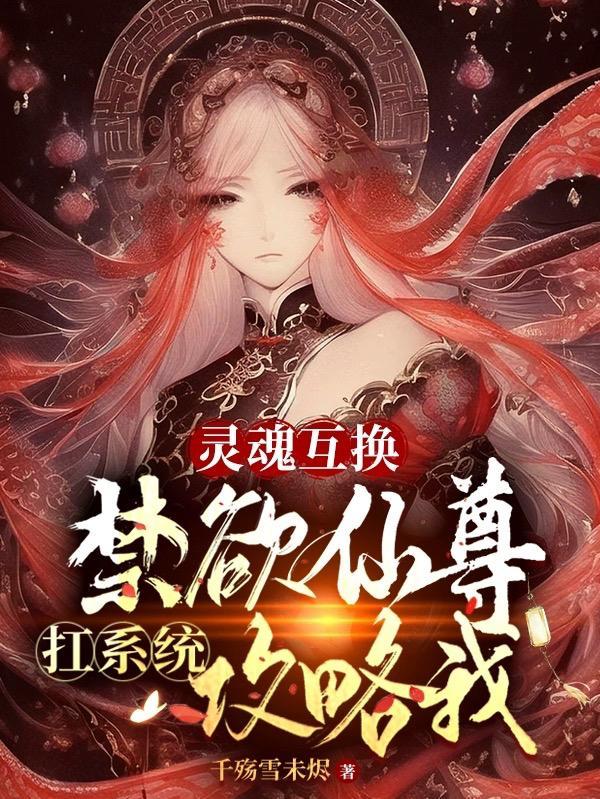富士小说>专业代理人图片 > 第11章(第1页)
第11章(第1页)
那天午后,一个男人拿着鱼竿正准备垂钓,却看见了一个小木盆,木盆里的凌伏以此刻正在哇哇大哭着。
周围群山坏绕,层峦耸翠,婴儿尖亮的哭闹声简直要响彻天际,让人想不注意都难。
江阁悬走到湖边,再往前方不远处就是一条悬崖了,他一边感慨这孩子命大,一边用竹子做的鱼竿把这木盆往回拨。凌伏以的额头上临走时被贾桑迎绑上了一条朱红色的抹额,以此遮挡那显眼的痣。
江阁悬把这婴孩连盆带人抱回去,家中的妻子聂试灯看见这个粉雕玉琢的娃娃,心里高兴的不得了。
聂试灯原本是石女,此生无法生育,不过江阁悬还是毅然决然的娶了她,怕她听见别人的流言蜚语觉得不舒服就带着她搬迁到了这里。
此处虽然有不少人家,不过住的都比较分散,彼此之间不会经常见面。
现在他们好像得到了上天的恩赐一般,这个孩子就像是老天爷送给他们的礼物。
夫妻俩一拍即合,准备养育这个孩子。
他们把凌伏以从木盆中放到床上,这才发现这孩子的体温烫的惊人,于是连忙让江阁悬去就近的郎中家请他过来为凌伏以看病,江阁悬马不停蹄的就去请了大夫,折腾了一整夜,凌伏以的体温才慢慢恢复正常,停止哭闹,安稳的躺在床上。
聂试灯准备给凌伏以换身衣服时才发现放在他心口字条,字迹遒劲有力且简短,只有三个字:凌伏以。
昏黄的煤油灯下,聂试灯小声的叫来丈夫,两人看完字条后又看着睡得香甜的凌伏以不约而同欣慰的笑了笑,他们这知道这就是那孩子的名字。
有了名字以后跟这世间就有牵绊了,就有根了。
他们没有改这名字,也不在乎什么名声,想着既然凌伏以愿意来到他们家,这已经很好了,以后等他长大了再告诉他的身世。
而且虽然他的名字不是他们取得,不过等到他弱冠的时候,就可以亲自给他取字了。
由于消息闭塞,他们不知道什么煞的故事,他们年纪也不算大,并不知道上一个煞的现世到底给世间造成了多少的苦难,幼时偶尔会听见村中的老人谈论,不过他们也都当时一个传说。
他们只知道他们自己的孩子,眉心有一个红色的痣,生的也让人移不开眼。
贾桑迎留给凌伏以的那条抹额,聂试灯也让凌伏以日日戴着。
两指宽的抹额,颜色朱红,正好齐眉盖在凌伏以的眉心,遮挡住那颗痣。
在聂试灯与江阁悬的悉心照料之下,凌伏以很快健康的长大了。
那一年,他十四岁。
每日晨起便去不远处的山头,趁着牧羊的人在树下小憩的时候去抓他家的羊又或者是偷喝他家的牛产的牛乳,等到动静太大把人吵醒,他就笑的一脸乖巧。
“林叔,我就是太无趣了,来这里找你玩而已,您不会生气吧。”
林柏每次都吹胡子瞪眼的看着这个捣蛋鬼,举起平日赶牛的鞭子作势就要打,这时凌伏以就会立马跑开,嘴里嚎叫着:“林叔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改天我偷我爹酿的青梅嗅给您喝!”
“你每回都说,哪一回拿来了,啊!欺负我的羊,喝我的奶,你这臭小子,我今非带着你去找你娘对峙,让她好好的教训你!”
凌伏以一听,顿时急了:“别啊,林叔,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求您了!”
凌伏以在前面跑,林柏在后面追,不过他年纪大了,根本追不上凌伏以那两条飞快的腿,只能跑一阵就停下来,看着凌伏以对着他做鬼脸:“再见了,林叔,我明天再来陪你!”
清亮的声音响彻山头,山脚下的人家早已习惯他们两个大清早的斗嘴。
林柏看着那清瘦的背影消失在山头,忍不住骂道“这臭小子!”
气着气着,又突然笑了。
回到家里,凌伏以风风火火的走到堂屋,一口气喝干桌上的菊花茶,抹了把嘴,就里里外外的寻觅,嘴里大声嚷着:“娘!娘!”
走到院子的菜地上,他声音依旧是不减,把院里的鸡吓得窜起来飞。
江阁悬正摆弄着地里的白菜,听见凌伏以的声音,答道:“你娘去集市了,今早上起来还问你想吃啥呢。”
凌伏以哈哈一笑:“哎呀,当时都睡迷糊了,我忘了。”
“没什么事的话,爹我就出去玩了。”
凌伏以笑的乖巧,一步一步的往后退,生怕他爹发现什么异常。
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江阁悬摆弄白菜的手一顿,抬头一看,凌伏以早已溜之大吉。
“凌伏以!!!”
“你又逃学,私塾的先生说你多少次了!!”
这魔音穿耳,凌伏以捂着都挡不住,但这声音还未停止。
“赶紧给我去学堂!否则等你娘回来,我让她把你屁股打开花!”
认命了,这书今天还真是非念不可了。
这方圆十里,就只有一个私塾,那先生青布长衫,八字络腮胡,教书的时候摇头晃脑,看见不认真的学生就伸出戒尺打一下。
这不,凌伏以进来的时候他正领着一帮小娃娃一句一句的念着书。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先生教一句,下面的人就有模有样的摇头晃脑的跟一句。
趁着蔡子衿转身的空隙,凌伏以轻车熟路的溜回了自己的座位。
等到先生再转身时,凌伏以就已经装模作样的顺大流开始读起来书来。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