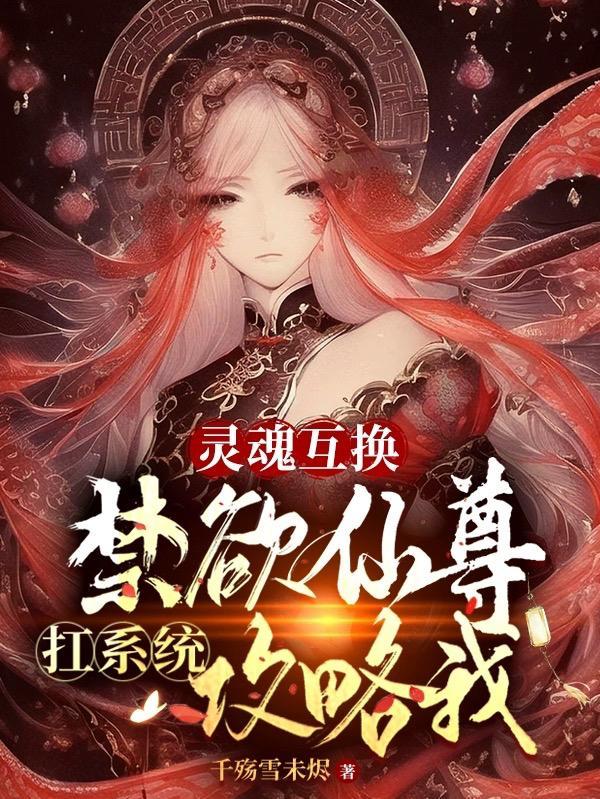富士小说>汉宫春慢好看吗 > 第15章(第1页)
第15章(第1页)
他清了清嗓子,脸上的表情多少也有些不自然。
不过随口问了一句,也是上位者身份的习惯使然。除非面见帝后,对待下头人他纵然温和,可也一直都是有话就说,还不曾掂量过语气轻重,话里话外是否会伤害到对方。况且他寻常与女人打交道,也多是别人顾忌他的想法,迁就着他的情绪来。
而今发生这种情况,一时间也不知道要如何去哄。况且“哄”这个字,在他刘郢十七年的人生字典里,好像还从未出现过。
申容从长长的睫毛之中瞟过一眼对面的人,这会索性就再任性一些,再放纵一些。
她顿了顿,依旧是低眸敛去神色,作势起身告退。
刘郢无奈张嘴应了声,想说些什么,但碍于实在没经验,就只能是吃了瘪一样抬了抬手,示意了许可。
头一回遇着这样的情况,只等到人走了许久,心里都总觉哪不是滋味。
翌日一清早,太子照常往兰房殿过来与皇后请晨安。与往常不同的是,他这日先在门口停顿了片刻,身后随侍的奴仆还有些好奇的,却也不敢多问。
只等到殿内候着的叔衣过来催,才往里进去。
郑皇后端坐主座,正由人清理了衣裳上的发丝。受过刘郢的拜见,便与他说了几句家常话,问了一天的安排、吃食一应。聊得不算久,就示意他回宫去忙自己的了。
储君每日的事也多,学功课、阅经书、替皇帝办政事,事情多起来的时候,从天亮忙到天黑,又从天黑忙到天亮,也不是没有过的事。郑皇后知道其中的辛苦,所以颇为贴心地不占用太子太多时间。
每日一清早就赶来问安,白日稍闲着些也会过来坐坐,孝心是绝对够了的。虽偶尔还好像隔着些什么,不如他未来媳妇这么贴自己,但到了这个份上,郑皇后已无所求了。
可今日出奇的,太子告退的步子慢了一些,还很是明显地瞅了眼旁室里头。
这副模样,郑皇后还能看不懂里头的名堂了?这些时日难得轻松一些,忘却了吴高侯的事,就笑问太子,“在找谁?”
太子一抬眉,面上又是漫不经心,顿了顿才说,“没见着储妃。”
还没成婚呢,就连太子自己也开始唤起“储妃”来了,看来这心里是认可了的。郑皇后乐得轻笑一声。婆家人倒是生出了娘家人的气派,只差指着太子鼻子笑骂了。
“这个傻姑娘啊,夜里服侍了孤歇下,晚上又不睡觉替你做吃食,连着两宿没睡觉,今早天不亮就倒下了,现下是喝了药睡去了。”
太子懵怔了一瞬,这才回过神来——她每日要学的东西也不少,还得操持着皇后的饮食起居,哪还有时间做那样复杂的东西……
他还未开口说些什么,座上皇后喝了口蜜浆,却是轻声提点了句,“还未成婚,你当守着些规矩的。”
话中意是就算心急,也不能私下去看望,不然传出去多少不好听,于女儿家的名声也不大好。
刘郢垂眉应下,“儿子明白。”
不过经过偏宫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停了步子,偏头看了有一阵。尽善随在身后,多少明白了太子的心思,上前耳语提了个意见,“要不奴婢找人进去看看?”
太子猛地回首,似乎被这宫奴突然来的话惊到。便摆了摆手,“唤苏泓入宫,陪寡人看书。”
兰房殿的外庭院里,太子宫的一群人离去,又恢复到以往的凄静,余下几个小黄门正用笤帚拂去地上的落叶。申容就站在窗后的暗面,眼波流转间,心思又不觉飘远了。
往前皇宫数十年人生,现在不过才过去短短数月,虽然如今谨小慎微,节奏还能掌握在自己手中,顺着想要的方向去发展,可她的心里却总不能安定下来,就怕半步差池,便是满盘皆输,覆水难收。
毕竟她可以依附的东西还是太少,申家于整个朝廷来说,也终究太过渺小……
到了下午,信平侯夫人带女钟元君入了宫,到兰房殿来看望郑皇后。
两个大人在后室说着话,钟元君略坐一小会就跑到偏宫来看申容了。
“我都听说了,她们说你是为了给太子做吃食,才劳了身子的。”有了上两回自然的相处,钟元君与申容说起话来,也逐渐亲近一些,不设防时,还能唤她一声“阿容姐。”
“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忙活那样久,也给我尝尝?”面上虽有些看热闹的心思,但嘴上到底还是没取笑的,就又转到吃食上。
申容自然地接过话,说“头一回下厨,手上也没个把握。回头等我熟练一些了,再做些给你送过去。”
“既然做得不太好,那太子是如何评价?”钟元君身上的机灵劲一股子冒了出来,到底还是忍不住打听打听她与太子之间的相处。
这些人似乎都留了一个眼睛在申容和刘郢的相处上,郑皇后是如此,信平侯一家也是如此,钟元君倒还算了,未经事的小女孩带着好奇也是正常,起先信平侯夫人象征性地来看她时,话里竟有些想打听的意味。
还好是郑皇后借着别的事敷衍过去了,不然这叫申容一个未过门的媳妇如何大肆宣扬?
这样的事说多了,是与不是,最后难免都会惹来口舌。
她便也学着郑皇后的,遇着不便回答的问题只顾左右而言他,“终归是耗费了一些心思的,这次从中生出了许多教训,下次也就能记着将其改正了。”说着也不留给钟元君太多思虑的时间,只将问题抛给她,“阿元喜欢吃什么,我也来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