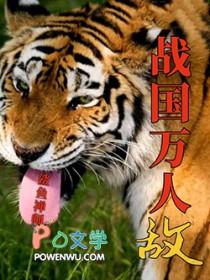富士小说>山河落娇红结局是什么 > 第87章(第1页)
第87章(第1页)
书房门被推开,郑渭和郑德并肩出来,几乎同时看见站在不远处的萧灏,惊讶地对视了一下。萧灏躲闪不及,忙行了礼,想就此离开。
“灏儿!”郑渭大声叫住他。
萧灏悔得头皮发麻,只好老实在原地待着。郑渭兄弟踱到他面前,果然,郑渭开口便问道:“我让你在江陵逍遥半年,那个沈休休,你追到了没有?”
“舅舅,您知道我愚笨,没那么快……”萧灏勉强应道。
“连这种事情都搞不定,真够笨的!”
郑渭叱道:“你饱读圣书,能文有悟性,都快二十岁的人了,却在男女之事上如此懵懂,何其笑谈?”
萧灏长这么大,第一次受舅舅这般训斥,隐忍着不发一言。郑德看在眼里,劝说道:“这怪不得灏儿。能与沈大人攀亲,那自然是好。只是男女之情不能急于求成,更勉强不得,只能慢慢来……”
“男女之事好比打仗,须得速战速决!我看,分明是沈不遇搞拖延战术,瞧不起咱家灏儿!”郑渭粗声打断,矛头转而指向郑德,“你也是,一心想让懿真当上皇子妃,让她跟在萧岿这小子屁股后面转。结果呢,人都贬走了,还当什么皇子妃?狗屁!”
郑德反遭一顿训,又情知郑渭的脾性,只有摇头苦笑。
郑渭回头又训萧灏道:“你是梁帝之子,堂堂四皇子殿下,若仅仅是显荣高爵待在浣邑,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下萧岿被贬走,皇上立嫡之事缓行,你虽不能接替萧岿,但这正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算了,沈家这门亲事不要也罢!”
萧灏闻听最后一句,脱口道:“我只喜欢休休!”
郑渭瞪圆了眼珠子,还想说话,郑德在一旁再次劝说道:“灏儿的性子,像极了咱家去世的妹妹,钻进死胡同硬是出不来。你越说他,他越死磕,你不说他,他反而自己会想明白。二弟,就随他去吧,说不定哪天沈家的孩子真的跟他走了。”
“唉,怕就怕灏儿这孩子毁在‘专情’二字上面!”
提起死去的妹妹,郑渭大是感叹,竟难以继续直然责备,摇摇头走了。
萧灏望着两个舅舅离去的背影,全身大汗淋漓,回到自己房间心头还怦怦直跳。
一夜纠结,对休休始终放心不下,翌日上午趁郑渭出去办政务,萧灏整肃衣冠又出门去了。
宰相府外,守门的侍卫一见是四皇子,全都躬身迎接。
“小姐在吗?”萧灏照例问。
“在在。”
萧灏闻言大喜过望。守卫正要去通告二夫人,萧灏及时阻止道:“来的次数多了,不用每次烦劳你家二夫人。我直接去萏辛院,只管通告一声燕喜便是。”
守卫称喏,忙着通告去了。
萧灏独自进入萏辛院,闻到一股药草的气息,面露惊讶。里面的燕喜揭着珠帘出来,萧灏便道:“怎么有药味,谁病了?”
燕喜施礼:“小姐染了风寒,病了三四天了。”
萧灏一惊,不断地责怪自己:“我是够笨的,早来几天就好了。”
“小姐得病,跟四殿下早来晚来没多大关系。”
燕喜跟萧灏熟了,也就不拘礼节开起了玩笑。在她眼里,四皇子既温和又俊雅,对小姐又体贴,比那个倨傲自大的三皇子好上十倍百倍。小姐自从认识三皇子起就霉运不断,还不如选择四皇子来得实在。
萧灏进了屋,便放轻了脚步,揭了软帘望向里屋。屋里窗子关着,窗帷遮着,半明半晦的,海红帷帐里静悄悄的没有声息。
“小姐可好些了?”他轻声问。
“好些了,只是刚睡着。”
萧灏连忙嘘声,蹑着脚走到茶案旁,低笑道:“这会儿不要喊她,等她睡醒了再说,我先在这里等等。”
“厨房的药快煎好了,奴婢端药去。”燕喜说完,便转身出屋去了。
萧灏靠茶案坐下,慢慢地饮茶。看案上整齐地码着两摞简册,随手翻开,见是兵书,不觉有点奇怪。顺着案头往下看,底下放着两口大藤箱,上面几卷同样是兵书史册。
他不觉暗暗想到:三哥最爱看这些书,休休的屋里怎么有这些?整理得这么细心,要送到哪儿去?
他将书册整理放好,坐了一会儿没事做,顺手拿了一本来看。
帘钩一响,燕喜捧着一个银盘子进来,上面盛着一只翡翠绿盖碗儿。见萧灏在那里阅书,她低低地笑道:“这些书本该送出去了,小姐一病,就暂时放在这儿了。”
“送去哪儿?”萧灏和气地说话。
“三殿下那里。”
萧灏一愣,自言自语道:“原来三哥已经回来了……”
燕喜以为萧灏知道,这会儿自知自己多嘴,忙说:“奴婢讲着玩的,殿下莫怪。药凉了,奴婢这就唤醒小姐。”
里面传来休休的说话声:“燕喜,是四殿下来了吗?”
萧灏唤住燕喜:“我端过去吧。”他接过银盘子,小心地进了里屋。
休休正要见礼,无奈头晕乎乎的,只好重新坐下,有些歉意地朝萧灏一笑。萧灏将药碗端给她,见她腮边有些红红的,恐是热尚未退,便伸手轻轻地向她额上拭了一拭。
“出了一身汗,不妨事了。”休休柔和地说话。
萧灏待她喝完药,接过湿巾擦去她嘴角的药汁,看着她的脸色,微笑道:“看见两大箱书,燕喜说是三哥的,莫非是玩笑话?”
“真是三殿下的,相爷让我整理,他已经回江陵了。我病了就搁在那儿了,过两天就送过去。”休休倒大大方方地回答,并告诉他确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