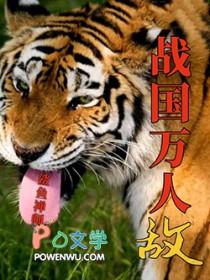富士小说>杀天子 TXT > 第59章 哭泣海域的沉船五(第4页)
第59章 哭泣海域的沉船五(第4页)
荀听好像明白了,现场就有一个“大腿”——活的南希伯国防司司长就站在他们面前,而他遇到困难却首先想到的却是“千里迢迢”地去找前队友。
荀听有些吃惊地看着却杀,心想,他是在介意么……
止心师比了个打住的手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你的帮助我可收不了……你要是给我出钱出资,卡佩斯不察觉才怪呢。我可不想被总统逮回去。”
却杀是相当理性的,他说道:“所以说我只能尽力,你们还是需要找一个无所顾忌的资金来源,寻求麦蒂的帮助或许是个很好的选择……试试吧。”
看着却杀的神色如常,荀听觉得又是自己多虑了,却杀根本没理由介意这种鸡毛蒜皮。
守夜真诚地和他们挨个道谢,有个族人前来告诉他,到时间敲钟了,于是守夜先行离开。
“这孩子心性很好,”止心师问却杀,道,“他们菲尼族有什么来源吗?我之前好像没听说过这个民族……不过也没差了。”
却杀只说道:“他们都是信仰怀霏的子民。”
止心师说:“怀霏?那个乜伽晟国的王子?他现在已经当上乜伽教皇了么?”
“……”却杀看着这个信息落后的“老年人”,道:“你脱离社会太久了,时政知识库该更新了。”
就在守夜离开不久,耳边传来悠扬的钟声。
守夜说,他从附近居民的口中了解到,这个废弃的守塔小屋曾经的主人是一家三口。
这家人会定时在傍晚到海边的小教堂鸣钟,并在午夜时分启动灯塔为海上的船只照明。几十多年来无一例外,他们已经成为这片海域的隐形的守候者。
但自从他们一家搬走消失之后,钟鸣和光亮就不再了。
大概是为了感激守塔人一家为他们留下了可以居住的地方,善良的守夜与族人捡起了守塔人的老本行,开始每天定期敲钟。
钟声与海潮声入耳,忽然,令荀听的心中一动。
他怔了半天,突然想起来,这座灯塔小屋的屋顶是红瓦砌成的。
绵长的钟鸣飘进他的脑海,将原主的那段在“沉痛灵魂”中苏醒的回忆引了出来——
“即使年复一年地面临混沌癫狂的火焰,我仍然会想念清凉的晚潮钟声,母亲归来时的笑容,与父亲烤制的牡蛎……和我那回不去的,红屋顶下的童年。”
“……从黑太阳教会里偷运出来的文献,与记录手稿,全部藏在了我与父母生活了几十年的故乡。”
海边、牡蛎、傍晚钟声与红屋顶。
……这里原来沉睡着这样的一家人的回忆。
原主努力逃离教会之人看管,将资料藏在了此处,同时他也将永远无法释然的仇恨与悲哀,与父母的骨灰一同抛进了大海。
荀听不知道,在他昏迷的时候,沉眠于海底的父母灵魂化作了两条白鲸,将他们生存于世的唯一一个牵挂,安全地送回了海岸。
那也是他们看儿子的最后一眼,之后,灵魂轻盈的光芒心满意足地熄灭在了海底。
灵魂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儿子备受煎熬之后,被强盗杀死在了送葬的路上,白木面具下的脸没有瞑目。他们眼里的“儿子”其实只是荀听。
可灵魂并没有那样复杂的辨识能力,他们看到的是:儿子生活得健康安好,他有一群结伴而行的朋友,愿意在危难时刻搭救他,他并非孤独一人。这满足了他们临终前的心愿,灵魂也因此可以消逝长眠。
而原主把骨灰抛向大海时许的愿望,就是让父母的灵魂安息。
巧合这东西鬼魅而悄无声息。
它又留下了一场荒谬而温柔的意外“骗局”。
荀听在钟声中失去了语言能力,他看向自己的双手掌心上那简单而清晰的纹路,这样被爱着的孩子,一定在出生时,手心就被父母欣喜地抚摸了一遍又一遍。
那时双鬓尚未花白的他们描摹着那些纹痕,在幻想未来的欢声、幻想牵着孩子学路时在沙滩留下的脚印,窥不见阻碍在命运中央的寂凉。
而从掌纹蔓延出来的那一条条通向未来的路,全部终结于被烈火焚烧过的灯塔与红顶房屋。
即使它们被守夜和止心师修复,也不再如从前了。
荀听沉默了半晌,缓缓地开口,说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有可能藏有一份记录文献,关于黑太阳的。”
在场人疑惑地看向他。
钟声似乎触发了这具身体的某种本能反应,让荀听的声音颤了一下,他说:“是一位英雄……不,三位英雄留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