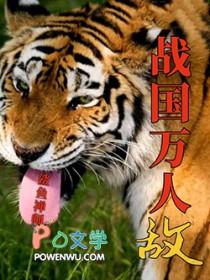富士小说>春鸢难觅 > 第50章(第1页)
第50章(第1页)
管事婆子看一眼主子的脸色,笑着安抚:“啊呀,哪个还能怪罪你,你说实话,只有得赏的份儿。”一块银子放在手心儿,那小厮千恩万谢地退下。
管事婆子进来回话:“姨娘,是好事儿呢。”府里得赏,无论如何都是好事儿。
文姝歪在那里,脸上的巴掌印儿已经肿起来了,涂过了药,小丫鬟蹲在跟前儿打着扇给扇风,她舒一口气,倦倦摆手:“是好事便好。”
好事?怎么不算好事呢,旁人不知辛家要嫁闺女的人家岂会没有事先打听,李家父子不睦,也就外头糊弄了好皮相罢了,辛家更不避讳,就这么大喇喇的亲自领了传旨的官儿来,哪里是为宣旨,分明就是明着来打李鹤桢的脸。
两家的亲事虽说是定礼合了八字,不好更改,可辛家的姑娘也不是任人好欺负的,你李鹤桢不听话,辛家自能捧个听话的来压制你。白日里才掉了辛家的面子,不必明儿个,夜里人家就能把不忿给还了。
李鹤桢要恼,又岂能不恼。
文姝只觉心情大好,肩头那道伤可没白挨。她蹙起的眉心也舒展开了,摇头屏退打扇的丫鬟,侧了侧身子,道:“我困了,就这么歇会儿。”
才要合眼,就听外头有婆子来报,说是有人送了消肿祛瘀的膏药来。
“谁送的?”红柳高声问那婆子。
婆子偷眉搭眼,她不敢说是自己收了二爷的银子,才来跑这一趟,只含含糊糊,夹着膀子小心回道:“是……是张姨娘院子里的一个小丫鬟。”
如今张姨娘管家,许是大爷有吩咐,张姨娘才打发人来送药的,红柳就要接过,却被管事婆子给拦了下来,“我来问他。”
后宅里的这些个藏藏躲躲的手段丫鬟们年轻没见过,她却见得多了。
“哪个丫鬟?若是张姨娘叫人送的,该是进屋到我们姨娘跟前儿回话才是,倘若不是……”管事婆子咬紧了牙,眯起眼睛发狠,“主子们仁慈,是不与你这老虔货计较,别叫我抓到你的膀子。”
文姨娘扺掌中馈的时候,这府里的婆子丫鬟们也都见过她跟前儿这位管事嫂子的手段,果断利索,狠厉快爽,没有过错也就罢了,只有了错处,再落在她手里,更没有好日子过。
传话的婆子吓得忙道实情:“是……是二爷跟前的丫鬟,说是二爷在外头听见咱们院子里姨娘在哭,恰好前些日子二爷得了好伤药,也不知道使不使得,就先叫我给帮着送进来了。”
“二爷倒是好耳力。”管事婆子讽她。隔着几道院墙呢,就是个顺风耳站外头,刮着往耳朵眼儿里钻的大风,也听不见里头的动静,明知这婆子扯谎,也猜到了她有受惠,管事婆子只想一下,还是叫人把东西给留下了。
临打发人走,还不忘斥责两句,叫她以后再不敢如此,传话的婆子唧唧索索应下,红柳气不过,嘴里还在嘟囔,又要把送来的药膏丢掉。
进去给姨娘回话,管事婆子朝外头看,示意这院子里有旁人的耳朵。
“你别声张,如今人家管家,咱们也不好得罪人家不是。”文姝笑着叫她不要莽撞。
“姨娘说的在理。”管事婆子笑笑道,“我想着,这事儿还得告诉小路总管一声,一来青山院从前就是小路总管在管,我只负责姨娘这边的差事,二来,我去求他,也算是有个服软的态度。”这态度自然是给大爷服软。
文姝笑她狡猾,“你去安排就是,我身上好疼,明儿个他回来了,问起我来,就说我疼死了。”
婆子只笑,知道她说的是气话,也不多回应。
红柳在后头进屋,犟起鼻子愤愤道:“我把那瓶药丢后院的花圃里去了,看着就讨厌,那位也忒过分了些,他明知……”明知姨娘的身份,却还要揪扯,分明是有意害姨娘失了大爷的心。
“你气成了葫芦,人家不知道,你岂不是白生气了。”文姝笑她,“别管那些了,你去打水,来伺候我洗漱,我眼睛的疼,脸上也疼,哪儿哪儿都没力气。”
红柳叫了个小丫鬟一起,屋里只剩下管事婆子和文姝两个,自有一番不叫人知道的悄悄话。
日子已出了伏里,白天尚有未消散的暑气,好在太阳落山,叫凉爽的清风吹过,外头就舒坦极了。
花坛里的木槿开了一阵儿,才败的几朵花苞还没人打理,张姨娘声大力气小,府里各处的婆子们也多不服她,今时她来管家,还不如文姨娘管着那会儿利索呢。
二爷守在西角门外头,一边又一遍地问那传话的婆子:“只丫鬟们在说,就没别人的话了?”他想知道的是文姝的态度。
那婆子被问烦了,连连告饶,也不回了,寻了个由头躲进周屋,假装忙碌。
二爷气恼她拿钱不办事儿,正要追进去再问,忽然瞧见里头出来人,还冲他招手,示意他进去。
将人带到人少的巷子里,管事婆子才从怀里拿出个帕子包着的东西,笑着放在二爷手里:“这是谢礼,我家主子说,谢您给的膏药。”
二爷举着东西,焦急地问:“她还好么?我听人说,大哥哥打她了?严重么?我叫我姨娘去给她请最好的大夫来?”
婆子婉言谢绝,哄他几句,千万嘱咐他不能声张。
二爷讷讷全应,目送那婆子走远,才恋恋不舍,回自己院子。
夤夜更深,打发走屋里伺候的丫鬟,二爷方敢把怀里的宝贝拿出来,映着明灯,展开帕子,里面赫然躺着一对银耳坠。
二爷先是怔住,忽然又喜,捧着东西高兴的一蹦三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