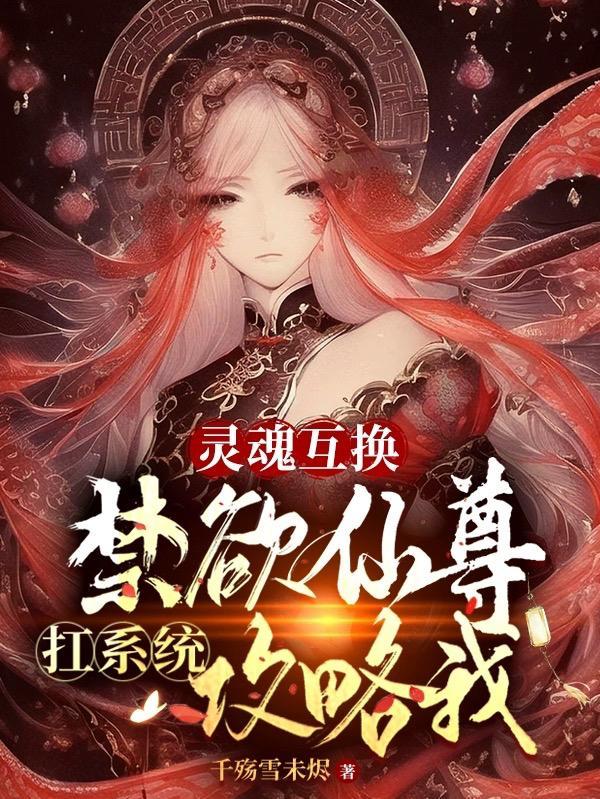富士小说>寒风吹吹着草木夜凉如水我单刀赴会 > 第28章(第1页)
第28章(第1页)
“明白了。”蔺长同替韩咏梅斟了一盅茶,“我看底方上有签名,之前给您开药的一直是一位叫钱礼的医生,为什么5月24号换成了赵强?”
“我也不知道。之前在药店坐镇的一直是钱大夫,但我那天去的时候钱大夫确实不在,只有从来没见过的赵大夫。我想着只是开个药,谁开都一样,就没在意。”
“那赵强回老家之后,您又见过钱大夫吗?”
“没有。”
“行,我记下了。”蔺长同朝这位朴实的中老年妇女点点头,表示自己问完了,端出一副儒雅谦和的笑。
北欧风的宫廷吊灯高悬于二人头顶,纱帘从通往花园的玻璃门顶上如飞瀑般垂下,再束于两侧的落地灯后。这座别墅看起来很有年头,装修风格却并不落伍,可见它在当时的年代有多么新潮前卫。脚下是巨大的羊毛地毯,蔺长同坐在沙发上,低头整理文件。
“蔺律师。”韩咏梅忽然说。
“您说。”蔺长同抬头看向她。
“我能……问你点事吗?”
“但说无妨。”
“你应该知道,秦与是晓飞的哥哥,俩人挺亲的。所以我平时找晓飞问点什么,他都替他哥打包票说一切都好。其实……哎,我也没什么太多想问的,我就想知道,秦与做律师这三年,还受过伤害吗?”
“秦与他……”
“我感觉你俩关系不错,你别向着他,给我说实话。”
蔺长同:“……”
您的感觉有点问题。
“嗯……”蔺长同斟酌了一下,“是这样,律师这个职业本身比法官更招仇恨,尤其刑事律师,收到匿名包裹或者恐吓信都挺常见。我不明白您说的伤害是指……?”
“字面意思,挨刀子流血那种。”
蔺长同一惊:“什么?”
花园里的梨树仍旧枝繁叶茂,但树上的团团白花却早已凋落。它们就像高贵又不耐暑气的冰凌,终将在奔赴夏天的路上融化。
秦与拾起一瓣梨花,轻轻抚弄,再举起来对着太阳端详,意兴索然。
于是他回身,透过玻璃门远远望进客厅,不知两人在说什么。
啧,有什么可回避的。
……
“当时他身上挨了四刀,有一刀还贴着心脏,差点没抢救回来。”韩咏梅小声说。
蔺长同怔了好一会。
他吸一口气把魂拉回来,意识到:“所以他辞职之前的最后一场庭审是……”
“3月20日,刘胡案。”
咚咚咚。
两人循声望去,秦与单手插兜站在通往花园的玻璃门后,另一只手还保持着敲门的姿势,背光的脸上是大写的不满。
蔺长同迟疑片刻,起身同韩女士道别。
他前脚刚走,后脚秦与推门而入,坐在他刚才的位置,“聊得怎么样?不满意我就给您找别的律师。好律师有的是,不差他一个。”
“挺满意的,你放心吧。”韩咏梅说。
“真的?”
“真的。”
秦与想起什么,“对了,您帮我找我爸要一套高中语文书行吗?最好是已经毕业的学生的,带着笔记的那种。”
韩咏梅说:“可以呀,干什么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