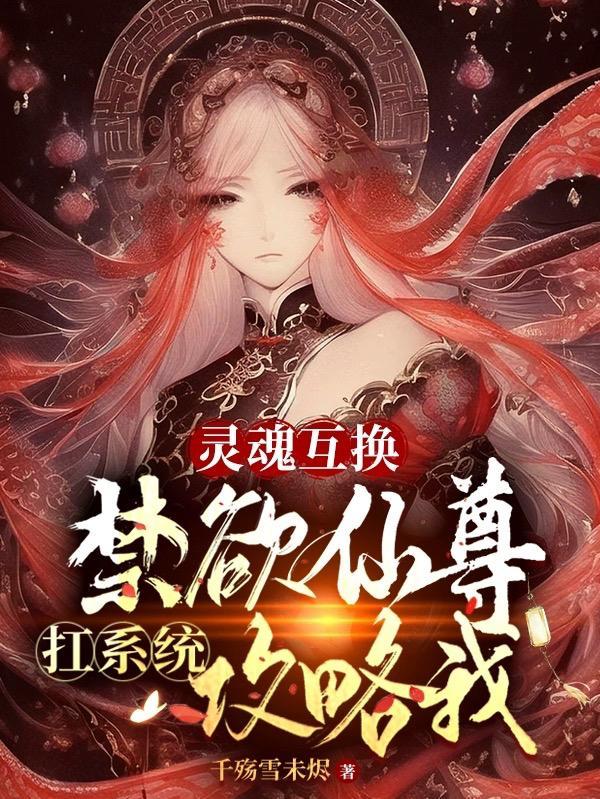富士小说>人鱼的诅咒为什么下架了 > 第59章(第1页)
第59章(第1页)
低下头,艾格能看到人鱼发际的长鳃。
两道鳃片在规律又轻柔地扇合,随着巫师话音落下,骨刺与锐光幽幽闪过,转瞬又隐没在了发间。
似是察觉到他的目光,人鱼抬头望来,艾格看到了它一如既往平静的脸。
一只蹼掌搭上了木桶,摩挲了会儿桶身,接着又按过桶沿。咕噜一声,失去平衡的空桶倒在了地上,慢悠悠朝他靴子旁滚了过来。艾格低头看了眼,脚尖一碰,踢了回去,它按住桶身,又轻轻推回。
艾格踩住了这只木桶,陌生的人类及语言的交流,似乎还没一只木桶更能引起它的兴趣。
雷格巴好一会儿没出声。
他像是不知道该不该继续了,看了半天水中悠然滑摆的鱼尾,最后还是整理出话语:“当然,我没有指挥的意思,你待在你的地方,任何地方,水池或大海。至少……至少,希望你听懂了这个。”他指了指自己,“友善的。”
随后他望着人鱼胸膛上那道分外显眼的伤口,从宽大的兜里摸了摸,摸出一个绿油油的玻璃罐子,继续表现善意:“这个。”
“草药。”他把瓶子放在地上,退后一步,“外伤用药。”
艾格认出了那个药罐,上次他从船医室拿走的那种,自认友善的巫师给他也留了一罐。
走过去,艾格从地上捡起了这罐药。
“外伤用药?”他向他确认。
“外伤用药。”雷格巴说,“可能不太好闻,但蛮有效。”
艾格将药罐放进了兜里,回头去看人鱼,那双灰眼珠也在望着这边。
“看上去,它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他朝巫师说。
雷格巴一声未吭,眉头比进门前更加纠结难解。
对着人鱼,巫师似乎也没其他招了,艾格结束了他的旁观,重新拎起木桶,池子里的水刚过一半,还未装满,他继续出门取水。
水声传来,雷格巴眼睛掠过池边的动物。
人鱼已经滑到了池里,只剩半个上身露在池沿之上,它注视着门边。白日晨光下,那双灰眼珠颜色偏浅,近乎透明,似乎只有平静,不见夜里的深沉,似乎——
原地踌躇一瞬,雷格巴跟上了艾格出门的脚步。
像是在检查监狱的每一根铁杆,他再度环顾这个水舱,玻璃窗扇,失修的木门,再到门上铜锁,出神的思虑让他一时没注意脚下,右脚绊上门槛,他晃了晃,下意识朝前方伸手——
那是一种见缝插针的职业毛病,不管有多冒犯,巫师那做惯了下药取血的双手总喜欢往人身上触碰,就像此时,比起更近的门框,他第一时间伸手去抓的却是前方的衬衫衣角。
快要碰到了,然而没等那个近在咫尺的背影躲开触碰,雷格巴手指一蜷,飞快地把手缩了回来。
这似有所感的一激灵全部来自脊背与后颈。
他撑住门框,转回头,迎上了志怪动物的一双眼睛。
那双灰眼珠正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看着他的手。
心脏擂动间,雷格巴看清了它的眼睛——昨天夜里的一眼,刚刚谈话间的那几眼,他直视过很多次那双眼睛,不是吗?但——他看清了志怪动物的眼睛,确信那双眼睛在这一刻比以往任何一眼都要清晰可辨——偏浅的灰,几乎透明。
铅石,烟雾,阴雨前的天空,诸多象征来源灰色,而那双眼珠不属于任何一种可以想象的灰。那灰色深邃无底,却并不自然,也不浪漫,那是一种褪色的、病态的灰,巫师联想到了古老秘本上那些不详且禁忌的咒语。
手上的汗毛在不由分说地根根竖起,他感觉自己的手掌像是刚从一个兽类的领地里缩回,而领地主人的一双眼睛正在判定那只手的偷窃。这荒谬的想象令他手指发麻,好一会儿,雷格巴才转过脸,看向已经提着木桶远去的背影。
他没有回头再去看那双眼睛,谨慎的两个退步,退到了墙壁后面。
失去脚步声,水舱周围的甲板就只剩沉默,雷格巴和远离门边的伊登对视片刻。
“……今晚你们不用值岗了,对吗?”他问。
“是的,轮岗。”
“后天继续?”
“是的。”说着伊登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你还想过来?”
“不。”这个词掷地有声,雷格巴把双手放进了兜里,过了片刻,又拿出来慢慢揉了揉,“我会离这儿远远的,离那种动物远远的。要不是——”他望了眼船舷边的背影,“要不是宝箱在船上,我会离这艘船也远远的,无知者才无畏。”
他转身欲走了,突然又退回一步。
“天知道这艘船怎么招惹上了那种动物,一个忠告,你那同伴听不进的忠告——随你们怎么享受你们的宠物时光,但,拜托,待在屋内时,至少把眼睛睁开,行吗?”最后他警告伊登,“叫醒他,别再让他在那条尾巴里睡过去了。”
巫师没打招呼就离开了,艾格在舷旁转头,只瞥到一眼他的背影。
那背影飞快拐了个弯,眨眼就消失在了缆绳纵横的甲板上,艾格在那仓促背影上品味出一点逃离之意,他抬头,望了会儿被那脚步惊起的几只海鸥,随后收绳提桶,走回水舱。
给水池注满海水,他拿出了巫师留下的绿色药罐。
拧开盖,嗅了嗅,草药已有用过的痕迹。
将这个药罐扔到舷外,艾格去了趟船医室,把另一个相同的绿罐子拿了下来。药草香料向来是巫师擅长的东西,神秘手段又防不胜防,他并不信任这个巫师经手过的药物。
那道伤口像是成为了人鱼胸膛肌理的一部分,放在一个体质稍差的人类身上,早该奄奄一息,但它行动间却像完全不为受伤所碍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