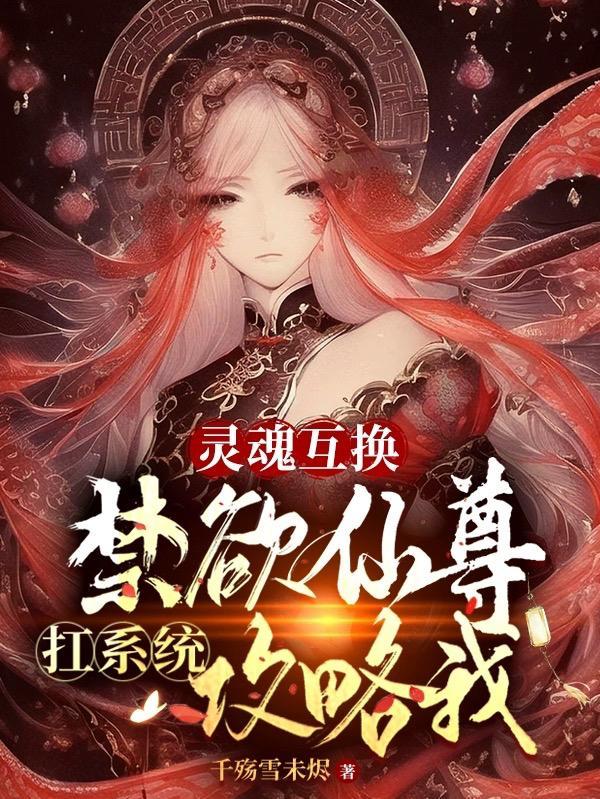富士小说>弥生夜澄昔 > 第17章(第2页)
第17章(第2页)
在船上被吹得心烦意乱,她干脆绑了个丸子头,刚刚才散开,一头长发带了自然卷,发尾几缕勾在手臂上,又被捋到肩后。
付迦宜没回头,背对着他问:“我们明天是不是要回去了?”
程知阙说:“不急,你想多待几日也无妨。”
“算了……无论待多久总归要走。”
“不舍得走?”
话里漏洞被抓住,付迦宜不想承认,迂回说:“没出来之前,你说自驾游会上瘾,看来在这方面有过不少经验。”
她讲得婉转,不乏似有若无的试探,想着力隐藏,实际没起到太大作用。
程知阙笑说:“你是想问我,之前有没有和其他人来过这?”
付迦宜轻喃:“……我不是关心,只是随便聊聊。”
“没有。只和你结伴来过。”他答得坦然。
海边风大,帐篷不能完全避雨,水珠落到皮肤表面,温润的触感。
他气息越来越近,近到她呼吸一再放缓。
头顶光影被遮住,付迦宜抬起头,瞧见他逐步靠近,缓缓侧过身,站在了对面,用背部替她遮风挡雨。
猝不及防面对面,付迦宜下意识重复那晚说过的话:“……我没那么娇气的。”
外面一道雨雾,看不太真切具体景象,他声音显得尤为悦耳:“在我这,即使娇气些也无所谓。我会护着你。”
他说会护着她。
出于一个教育者最基本的责任吗?
付迦宜并非不明事理,传道受业解惑哪一样不比“保护”责任重,她既承了那三份恩情,合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承下这份。
但她似乎无法做到,也无法顺其自然为其归类。
付迦宜后退一步,伸出手,拽他腰际雾蓝色的衬衫面料,丝滑的绸感,薄薄一层,光是攥住似乎已经耗费了不少力气。
她拉他过来,看着他的眼睛:“少淋些雨,你也需要被保护。”
周遭倏然变安静,谁都没再开口。
插曲一过,雨差不多也快停了,岸边多出一艘游艇,有个中年男人拎着钓鱼工具,坐在折迭椅上排兵布阵,鱼竿一端很快被抛下水。
程知阙目光所及,瞧着这场面,无端轻笑一声。
付迦宜轻声:“怎么了?”
“没什么。”程知阙收敛目光,低头注视她,“突然觉得你那天提的捕鱼方法不错,可以留着下次用。”
从卡西斯镇回来,付迦宜在家休整一天,隔天带着从外面买回来的礼物去找安维尔。
前些日子他借给她一本卡普斯汀的琴谱手稿,她特意来还礼。
即便不是第一次到隔壁做客,付迦宜还是觉得这房子从装修到布局都太冷清,没有一点烟火气,人待久了会很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