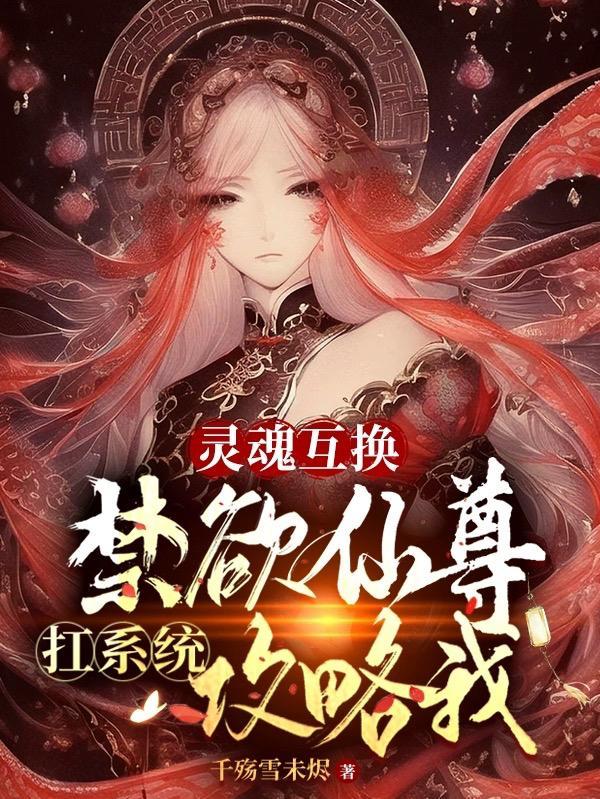富士小说>汉宫春慢好看吗 > 第19章(第1页)
第19章(第1页)
所以她从一开始就要比申容更懂里头的门道,哪怕现在的申容已有了一次教训,在某些地方也比不了她。
就好比这简单的问安,田家女知道要更早往天门殿过去,为了不多打扰到天子,三日一次问安即可;皇后这边就来得更勤了,同申容一般——每日卯辰就要过来的,就算梳头整衣这些活有申容在做着了,她也能毫不尴尬地杵在一旁,有活就做、有能开口的话就接、要安静的时候,也能恭顺得就像这兰房殿内的宫女一样,静静地守着。
哪怕是面对申容也是这样,两个都还未过门呢,就如郑皇后给她立的下马威一样,与申容做小伏低地行礼问安了。
要不是申容还知道回礼的规矩是什么,倒真像是刻意在打压她一样。
这样的人实在厉害。若不是没有办法,定然要坐上这储妃的位置,又为了之后保全自己同家人,她还当真是懒得费心思去同她较劲。
“阿容过来与孤篦篦头。”郑皇后还是多亲申容一些的,毕竟已有珠玉在前了,往后人要再想按着这条路去巴结,总要难上一些。
而且这事还难把握分寸。过了头显得假,做不到位又起不到作用。若想要在夹缝中求得一线生机往上爬,就只能默默等待时机了。
可申容又怎会给她这样的时机?
甚至还颇为和睦地与郑皇后提了意见,“婉儿姐我实在喜欢,不若就让她早些搬进来,与我住一起做个伴吧。”
郑皇后柳眉微微一簇,又说到了尊卑有序之上。“就算情如姐妹,可哪有妾这般没规矩的?怎么能和未来储妃住在一处?”
“娘娘~”她索性靠到了郑皇后的膝上,由她的手自然而然搭下来,抚着自己额角的碎发。
到了这个份上,偶尔撒撒娇,就更显亲密了。只有完全的信任、不设防,才是将对方真的当做了家人。大家闺秀的得体,那都是对外人做的。到了郑皇后跟前,定要有所不同,才能显得区别对待。
郑皇后就又嗔怪地唠叨了申容两句,最后才无奈应下。
末了还是不忘提醒她态度要强硬一些,就算田家女也是个温顺的,但以后后宫之中难保就不会出几个欺软怕硬、横行霸道之辈,到时候她要是再不立威,就难服众了。
皇后这些话说得真心,申容也就起了身,很是认真地听着训。
只有让田婉儿入宫,不再让田家其余人干涉,才更好地看管住她。
这些时日有了郑皇后的许可,申容每日需做的事里头还多了一项,便是前往北宫与太子读书。
有时午间刘郢过来兰房殿用饭,小坐之后就带着申容一起回太子宫了。离开的时候,田婉儿就与兰房殿的那些宫女老媪们一同相送。
她实在恭顺,恭顺得在人群中没了一点特别。这样的恭顺其实还有些像刚入宫的申容。而再往远了说,其实又是刚入宫的申容效仿了上一世的她。
申容不禁回头望了她一眼。两个年轻女儿家的眼神对视上,明明年纪更大的田婉儿倒带了畏怯,首先谦卑地低下头去。
她的心中却并不好受,仿佛从田婉儿身上看到曾经慢人一步的自己。
即便憎恶,但一旦感同身受,就忍不住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争来争去,谁赢谁输,终其一生费劲心机,虚伪渡过,最后当真就是快活的吗?这念头不过稍纵即逝,她忽得清醒,却更憎恶自己的愚善。身处皇城,尤其身后还牵扯到前朝,如若不争,死的就是自己同家人。
她没必要,也实在没有这个功夫考虑她人的处境。这里头本就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
……
苏泓今日也在含丙殿,同前几次一样,他在底下替刘郢完成本该是他的事,刘郢就在主座同申容并排坐着,同看一卷书。
《庄子》其实是她早就读过了的,在绥阳老家就看过不下数十遍了,上一世在皇宫里也是来来回回的读。这会却要在刘郢面前装懵懂无知,仔细听他念给她听,为她耐心解释。
她脸上绽放出来的笑就更加和煦了,仿佛一个年长者在看垂髫小童,还能看出几分可爱。
可这笑落到刘郢眼中,却是女儿家对自己的崇拜与仰慕,有“年龄”和“绥阳城来的”这两个刻板的印象,就算后来另眼相看一些,却也总觉得她还是明白得太少。
就算有时候能耍些小聪明又如何?真到了这些大道理上,还不是得仰仗着自己?
这么一经误会,心中的成就感就更深了,对申容也愈发黏腻,原本只读半个时辰,往往讲得远了,到申时都不肯放人。
直到后来连郑皇后都看不下去了,派了叔衣亲自来传话:“年少是易情浓,可怎么也得顾忌着礼数,谨守纲常的。”
不能明言指责太子,就当着太子的面给了申容重话,“申娘子可是忘了时辰?如何都不提醒殿下?非得闹得满宫闱都知道了,脸上就光彩了?”
申容就垂下了头,认真揽下错误,“是容错了,下回定当注意着些。”
太子一听这话当即就不大高兴了,好容易在申容面前建立起几分伟岸的形象,现在还让个女人替自己抗罪,多少非大丈夫所为,也就立即将错揽了回去。
“是寡人留着她的,说得久了难免忘了时候。回去与母后说,明日寡人亲自去认罪。”
储君都这般说了,叔衣就算在宫奴里地位再高,也终究是个宫奴,不免迅速伏身贴地,应下刘郢的话。
“是,殿下。”
这回就是连申容都忍不住感慨了,郑皇后真不愧能稳坐这么多年的后位。派叔衣过来训她这一招,用得实在是自然又妙。不仅提醒了太子要记着规矩,也惹得他对自己更多了几分怜惜。